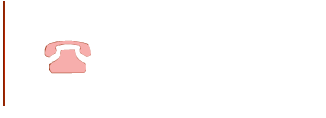作者:青山湖区人民法院 胡恋梅 发布时间:2012-10-09 11:16:22
新《公司法》第18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股东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程序、适用条件等进行了规定。其立法本意是为了更有效地救济和保障股东权益,但是这种救济手段对公司和股东却是一把双刃剑,操作不好就会两败俱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二)》)虽然厘清了此类纠纷的相关程序争议,但在司法解散的实质认定标准上仍然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法院如何理解适用公司法及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定来处理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纠纷也成为民商事审判实践的难点之一。
一、问题的提出—从新公司法实施后的二个相关案例切入
案例一 陈某诉浙江西山泵业有限公司、上海西山泵业有限公司解散案
陈某与吴某系夫妻关系,有亲子小吴,大吴为其继子。大吴为浙江西山泵业有限公司、上海西山泵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2001年吴某去世后,各继承人对其财产进行了分割,陈某和小吴分得两公司50%的股权,大吴及其他子女分得另外50%的股权。由于陈某与大吴产生矛盾,浙江公司、上海公司无法召开股东会议,公司股权一直未变更。连续三年来陈某、小吴未能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两公司三年来也从未向股东分红。陈某、小吴的法定股东权利被剥夺。公司股东之间矛盾很深,已经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于是,陈某向温州市中院起诉,要求解散两家公司并得到法院支持。担任两家公司董事长的大吴认为,自己没有剥夺陈女士等股东的权益。企业年年盈利,两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为职工就业、国家税收、社会慈善事业作出不少贡献,法院不宜强制解散两公司。在二审程序中,浙江公司提供了当地政府及其部门的多项说明文件来证明该公司的盈利现状及社会效益,但由于各自占有50%股权的两方股东之间矛盾已无法调和、在任何事情上包括是否延长经营期限的问题上也无法召开股东会议解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浙江公司和上海公司被依法解散。
案例二 博星公司等诉三毛公司股东请求解散公司案
2001年3月,博星公司出资1950万元、博德公司出资45万元、董某出资5万元、三毛公司出资2000万元,四方共同成立博华公司,从事基因芯片技术开发服务业务。根据公司章程约定,先由三毛公司委派人员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1年。同期,根据合同约定,博星公司应向博华公司转让“肝炎基因芯片技术”,但双方均未按约履行。经法院判决三毛公司亦不履行法人代表的手续变更义务。2006年6月,法院判决博华公司(仍由三毛公司人员担任法定代表人)应当提供公司会计账簿给博星公司查阅,博华公司亦未履行该生效判决。此外,根据工商年检报告显示,自2001年3月博华公司成立以来,公司历年经营亏损,现已无主营业务收入,处于停业状态。三原告诉称,博华公司由三毛公司长期控制,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处于僵局状态,现公司经营管理已发生严重困难,请求判令解散博华公司。被告和第三人辩称,如博星公司向博华公司履行返还2000万元技术转让款的义务,公司经营状况就会好转,故不同意解散公司。法院经审理认为,博华公司虽然处于僵局状态,但仍然存在摆脱困境的可能,遂不予支持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述案例均是根据新《公司法》第183条的规定由法院受理并作出判决的新类型案件。案例一的特别之处有三点:一是被解散的两家公司资产过亿;二是涉及众多利益主体,庭审中公司一方还提供了当地政府及其部门的多项说明文件来证明该公司的盈利现状及社会效益;三是纠纷持续时间长,在法院受理解散请求之前两家公司的股东之间在三年内已经经历了数场诉讼,直到省高院做出终审判决解散两公司。因此,该案例中的诸多争议点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司法解散之诉提供了极好的范例。案例二的审理则直接涉及公司法对于“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理解和认定,该案法官在立法并没有对“重大损失”、“其他途径”进行界定的情况下依据法理对之进行了很好的诠释。虽然上述案例中的一些程序问题在《公司法解释(二)》中得到了解决,如管辖、当事人诉讼地位等,但司法解散公司的实质裁判标准却仍然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取得共识的争点问题。
二、司法解散公司裁判标准中的争点分析
(一)公司僵局与公司解散事由之辨析
新公司法第183条规定的法定解散事由并未引用公司僵局的概念,但我国实践中将公司僵局与司法解散事由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的做法却相当普遍,如此势必偏离司法解散制度保护股东权益的初衷,因此,有必要对二者进行辨析以准确理解司法解散公司的裁判标准。
公司僵局是英美法上的概念,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定义,公司僵局是指“公司的活动被一个或者多个股东或董事的派系所停滞的状态,因为他们反对公司政策的某个重大方面”。 《麦尔廉—韦伯斯特法律词典》则将公司僵局界定为:“由于股东投票中,拥有同等权力的一些股东之间或股东派别之间意见相左、毫不妥协,而产生的公司董事不能行使职能的停滞状态。” 虽然两本权威法律词典的解释过于简单,但均概括出了公司僵局的核心意思,即公司中的两派或数派持有相同数量表决权的股东或董事相互对立、相互牵制,公司陷入表决僵局。
国内最早研究公司僵局的学者赵旭东教授也是在表决僵局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 由其参与起草的《中国公司法修改草案建议稿》中便有专门的一条列举了公司僵局出现的情形, 但新公司法没有采用此概念,也没有列举与公司僵局相关的情形,表明新公司法规定的司法解散不以公司出现僵局为前提,它也关注其他事由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否发生,这与英美法上将公司僵局作为提起解散之诉的原因的立法例显然不同。
因此,笔者认为,把新公司法及《公司法解释(二)》规定的解散事由理解为公司僵局是不准确的。公司僵局并不必然导致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在出现严重困难之前僵局可能被打破,针对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也不只是司法解散一种,只是当穷尽其他措施无法化解僵局时,解散公司成为最后选择。此外,多数派利用占优势的表决权实施的股东压制行为与公司僵局无必然联系,这种案件在公司解散诉讼中也占到一定比例,将公司僵局与我国规定的司法解散事由等同考虑必然会截断这类案件诉诸法院的途径。
(二)“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之判断
目前,对于新《公司法》第183条所规定的“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事实构成要件,尚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司法认定标准。结合前文的两个案例可知,审判实践中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判断,一是以公司经营状况恶化为认定标准。一般是根据公司资产负债表、工商年检报告或通过司法审计。二是以公司治理发生僵局为认定标准。如查明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处于严重僵持状态,导致公司治理结构上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就可以认定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案例一正是以此为判断依据的。但由案例一和案例二的判决结果可知,两个认定标准是结合使用的,而且有的案件中法院会偏向于考量公司经营状况是否恶化,如案例二所涉博华公司自成立以来便处于连年亏损状态并已停止主营业务,且公司股东会无法正常召集,即使召集也不能达成有效决议。因此,博华公司的状况符合“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事实构成要件,之所以不支持原告方解散公司的请求,在于有其他途径使公司的经营状况好转。
在目前的立法条件下,笔者也赞同综合考虑公司治理层面的困难与公司财务层面的困难两方面来判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形,但是,除了上述两个层面的理解角度以外,当多数股东不同意解散公司,只有少数股东认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而向法院提起司法解散之诉时,法院的认定标准便模糊起来。尤其是实践中大股东滥权严重侵害其他股东利益而公司运营正常的情形并不少见,如股东遭受不公正欺压、公司资产被滥用或浪费、公司法人人格被不正当利用等,此时公司的经营管理未必陷入严重困难,但当股东以上述事由请求法院解散公司时却可能得不到支持。
因此,在解散公司只是少数股东的意愿时,法院的判断是否会与多数股东正常合理的商业判断冲突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相关司法解释不仅仅须进一步明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具体情形,并应扩大解散事由,应对实践中出现的因多种原因引发的司法解散要求,增加对小股东权益的保护,尤其是对于股东压制的救济。
(三)“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之判断
对于股东而言,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是仅指股东、公司的自力救济,还是也包括行政救济及仲裁救济等其他途径,如果是前者,要不要股东、公司穷尽一切除司法外的救济途径,现行公司法没有规定。对法院而言,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是指股东起诉时法院受理的前提条件还是依法判决解散公司的实质要件,即法院裁判的标准在审判实践中也有不同理解。一种意见认为股东起诉请求解散公司之前,必须用尽其他救济程序,即股东必须依法通过诉讼行使知情权、盈余分配请求权、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无效、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请求公司收购股权等,只有在通过这些程序后仍无法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困境的,才能提起解散公司之诉。另一种意见认为,对股东提起解散之诉不应设置前置程序,只要事实上构成“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公司股东即可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应考虑予以支持。
对此,“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规定表明我国公司法对于解散公司所持的审慎态度,体现了公司维持原则。从立法技术层面上分析,这是针对该条款关于公司解散条件成就的但书,对于该项但书的审查应当是事实审查,而并非程序审查。因此,一方面不能将“通过其他途径”机械地理解为前置程序,未穷尽其他途径,股东就不得提起请求解散公司之诉;另一方面必须切实审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困境的现实可能性,如从事实上确认“通过其他途径”解决问题存在客观可能性的,就应当从实体上驳回股东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例二所涉博华公司案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该案中,法院经审理认定各方股东各自未切实履行与公司经营管理救济密切相关的生效判决和仲裁,且确定一旦履行,公司僵局和经营不良的状况仍存在改观的可能。因此,履行已生效的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已构成上述但书所规定的通过其他途径可以解决的情形,即使博华公司已经符合了“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事实构成要件,法院最终还是驳回了原告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尽管有司法实践已经对于法律规定作出合乎法理的理解,但为消除歧义,今后的相关司法解释还必须进一步明确对“其他途径”的立法,提高司法运作的效率。
三、司法解散公司的裁判标准考量
(一)理论支持
1、公司自治与司法干预的平衡
司法权介入公司自治的首要障碍就是公司的法人格问题,但基于公司自治的局限性和公司社会责任的凸显,各国的公司自治都未排除法院凭借司法权对公司事务的干预,关键在于司法干预的范围、方式与深度。但是,公司自治与司法干预之间的平衡点并没有一个明确而绝对的界限。尽管如此,美国的商业判断规范仍然可以为我国提供一个极好的例证。根据该规范,“法官不干预由公司管理层做出的商业判断,只要该决定是经过某种程度的勤勉和谨慎以及不存在欺诈、非法或利益冲突”。 这一规范的理性基础之一是法院不适于评价商业决定,但涉及欺诈、不诚实或其他自利的行为时,司法系统会坚决地采取行动。实际上,这一理念力图要实现的是市场机制和司法机制的平衡,也决定了英美国家在构建司法解散事由时所做的立法选择,即法庭颁发解散令主要考虑两种情形——公司陷入僵局以及股东受到严重压制。因此,对僵局以及压迫行为的认定常常成为法官审理此类纠纷时须首要解决的问题。相比之下,在大陆法系国家包括我国的公司立法中,司法解散的理由多着眼于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法官往往需要判断公司经营是否遇到显著困难或重大损害。如果说英美国家主张司法对公司经营领域的合理性审查,那么大陆法系国家则趋近于合法性审查,这两种态度也恰好反映了两大法系国家司法裁判权介入公司内部事务的范围与深度的差异。
2、对股东合理期待理论的修正
美国的封闭公司问题权威F. Hodge O’Neal 教授指出,在封闭公司中,“股东成员的基本预期是能够参与公司的管理并能被雇佣以获得报酬,即使没有就这一预期达成明确的协议。而资本多数决原则的绝对适用势必挫败股东的合理预期”。 具体而言,资本多数决原则决定了在股东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占有多数资本的股东会利用甚至滥用这种优势使自己的意志最终成为“公司的意志”,“合法、合情、合理”的实施侵害公司利益和压制中小股东的行为,一旦多数股东对公司进行不正当地控制,公司异化为控制股东压制榨取小股东利益的工具时,小股东的这种期待利益就将落空,法院在提供公司强制性解散救济时主要也就以股东合理期待利益落空作为判断标准。
一般来说,股东合理期待落空的情形主要有:1.股东被排斥担任公司的管理人员或被剥夺参与公司事务的管理;2.控制股东欺诈、侵害其他股东利益行为发生;3.封闭公司股东之间信赖关系的丧失;4.公司陷入僵局,严重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持续下去会给股东利益带来严重损害。 但由于这一标准仍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且引发滥诉现象,这一理论的效用也因此被质疑和反思,长期采用这一理论的英美法系国家最终采用替代颁发公司解散令的措施来弥补其缺陷。 因此,英美法系国家的法院在认定公司是否应予解散时已充分考虑到采用替代性救济措施的可能性,适用股东合理期待落空原则的结果已根据个案具体情况而具有了一定的灵活性与多样性。我国没有明确引入股东合理期待理论,但实践中上述导致股东合理期待落空的情形在我国均有相应案例发生,而立法在应对这些情形上略显不足,如判断股东权益是否严重受损、受损股东利益的补偿是否与解散公司所保护的价值相当均缺乏明确的立法支持。因此,笔者认为,借鉴这一理论来统一司法解散的裁判标准,同时设计一系列替代性救济措施来约束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也是完善我国司法解散立法的必然路径。
(二)扩充司法解散法定事由以应现实之需
1、法定事由应突出对股东权益的保护
虽然限制解散判决的作出已成为各国公司立法及实践的发展趋势,但各国在对待解散事由的适用上一直呈现出两种态度。
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更注重于对股东权益的保护。依据《美国示范公司法》第14.30(2)条的规定,申请解散公司作为救济手段的股东必须证明公司存在以下几种情况:董事会或股东之间出现僵局,前者造成公司利益将要或正在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或者公司事务已经不能根据全体股东的利益得到处理,后者造成不能选出任期已经届满的董事继任者;董事或实际控制人正在或将要实施非法压迫或欺诈行为;公司资产正在被滥用或浪费。 因此,不仅仅是公司僵局,类似于股东受到压制、排挤的不公平损害行为以及股东之间失去信任都可以成为法庭颁发解散令的依据。
相比之下,大陆法系更强调公司的整体性,一般是在公司因内外部原因难以继续经营下去时,股东可起诉要求解散公司,其立法中的事由也习惯于用“不得已”或者“重大原因”来进行框定。例如《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 61 条的规定:如果公司所追求之目的不可能达到,或者存在其他由公司情况决定的、应予解散的重大理由,公司可以通过法院的判决而解散。 日本商法深受德国的影响,其有限公司法第71条第2款规定:于下列情形,有不得已事由时,集有公司资本1/10以上的出资股数的股东,可以请求法院解散公司:1、公司业务执行陷入困境,己产生公司难以挽回的损失或有产生此损失之虞时;2、管理、处分公司财产显著失当,危及公司存在时。
显然,我国公司法对于法定事由的规定深受大陆法系国家的影响,同样侧重于从公司整体利益的角度对于可能导致解散的事由做出判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作为申请解散的法定事由似乎是以股东利益为基准,但由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困难并不能涵盖股东受到压制、排挤的情形,实际上淡化了对股东权益的保护,无法应对实践中股东遇到不公正侵害而只能求助解散公司的案件需要。
2、法定事由应有明确简单的判断标准
新公司法第183条所指的“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其含义应包括公司权力运行发生困难及公司的对外经营活动发生困难两种情形,即应将公司的“人合性”与“资合性”要素均作为解散事由的判断标准。
新公司法出台以后,各地相继出现司法解散诉讼“第一案”,最终判决解散的案件还是比较少的。在这少部分案件中,判决理由又多以公司对外经营陷入严重困难为标准。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法院对于此类案件不再拘泥于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判断,而是将“经营”、“管理”以及“股东利益”结合起来进行考量,并侧重于“股东利益”,实际上也就是兼顾到“资合性”与“人合性”要素的统一,并侧重于“人合性”要素。本文所选取的案例一中浙江一起在当地享有一定知名度的亿元家族企业被强制解散的案件便体现了法院对于这一判决理念的追求,这也与解散之诉保护股东权益的初衷相呼应。
3、法定事由的具体情形仍有待扩充
从目前看来,《公司法解释(二)》针对“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所列举的具体情形过于侧重股东或董事之间的僵局考量,而对于股东权益的保护和公司解散的替代性救济措施却明显考虑不足。总结目前司法实践中公司解散类案件的规律可知,以下三种情形常常成为导致公司解散的关键理由:(1)公司股东或董事会僵局;(2)股东投资设立公司的目的无法实现,且股东通过其它合法途径退出公司受阻;(3)少数股东被控制股东或大股东们利用优势地位排挤、压迫,且通过其它合法途径退出公司受阻。其中,第(2)、(3)种情形实质上便是股东压制的问题。公司董事或其他管理层的人员对其他股东实施非法行为,故意剥夺其法定股东权益,而受害股东所持有的股份不足以对公司事务的进行起决定性作用,也无法与大股东形成有效的抗衡,此时股东投资设立和经营公司的合理预期得不到满足,受害股东据此要求解散公司的请求应给予支持。实践中这两种问题往往交错在一个案件当中,增加了公司被解散的可能性。如本文案例一便是公司僵局与股东压制情形兼而有之,尽管公司营业状况良好,但人合性要素已经完全破裂,这才有了亿元家族企业被判强制解散的结局。因此,司法解释对于公司解散救济法定事由的规定也应涵盖到公司僵局以及股东压制这两方面的情形,才能真正实现对股东权益的保护。
(三)引入替代性救济措施弥补商业判断缺陷
在权衡资合性与人合性孰重孰轻的问题上,如果以“资合性”要素的丧失作为主要判断标准,则反映出我国法律规定过于注重公司的整体性而忽视股东个体性的特征。但是,若以人合性要素的丧失为主要判断标准,则正如西方学者所言,“若公司兴旺发达,基于公平的原则解散公司就犹如宰掉可能生出金蛋的鹅”。 为保护股东的合理预期,法官不得不面临两难选择。西方国家在解散之诉中所遇到的尴尬同样是我国公司立法不可回避的问题。
1、国外替代性救济措施的立法实例
英国1986年《破产法》的122(1)g项规定:法院认为解散公司是公平和合理的,就可以解散公司。 这一规定赋予了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而自1985年英国《公司法》规定了比较完备的不公平损害诉讼制度以后,解散措施便与不公平损害救济制度相互补充为用,两种救济方式的竞合问题在1986年《破产法》第125(2)条得到阐述,即对于申请人来说,如果存在其它的救济措施,公司不得被宣布解散,法院会认为申请人不寻求其它的救济措施而要求解散公司是不合理的。 因此,只要公司解散能够被一种可替代性的法律救济所代替,如命令公司或控制股东购买受害者的股份、修改公司章程等,则股东的申请解散请求一般会被法庭驳回,但是这些替代性法律救济并不排斥股东所享有的要求法庭颁发公司解散令的权利。
与英国类似,美国于1991年在《美国示范公司法》中增补第14.34 节,将指定购买全部股权(也称买断)(buy-out)这一替代性救济措施成文化。该节规定,提起解散之诉后,公司一个或多个股东可在诉讼提起后90天内选择是否购买提诉股东的全部股份。一旦公司或股东选择买取股东股份,即不可反悔。
可见,尽管股东可以向法院请求解散公司,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请求会很容易得到法院的支持。西方国家法院不轻易颁发解散令的司法态度也体现了立法者和司法者对于平衡理念的追求,即对于个人权利的救济和社会利益的最大限度维护之间的平衡,我国在构建司法解散之诉时,也应当坚持这种平衡理念的指导,以期为维护股东权益、公司利益及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提供制度保障。
2、对我国引入替代性救济措施的建议
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替代性救济措施,法院作出强制购买股份、指定临时监管人等各种强制性裁决没有法律依据。但《公司法解释(二)》对于替代性救济措施的采用已有了回应,其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协商同意由公司或者股东收购股份,或者以减资等方式使公司存续,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新公司法中的一人公司制度、股份回购制度等也为该司法解释的实施提供了配套制度。因此,法院在裁判是否解散公司的过程中,应注重具体考量是否有代替解散公司的其它救济措施。主张将调解确立为我国司法解散诉讼的必经程序,其目的也是在于通过调解获得解决公司僵局、救济受压制股东的替代性措施。这种替代性措施并不是指程序意义上的替代审判纠纷解决机制,而主要是指避免解散公司的某些救济方式,如请求命令变更公司章程、请求判令公司决议无效及请求回购股份等。这些措施可以使法官在权衡资合与人和要素的基础上,选择适用其中一种或多种措施来尽量保存公司的营运价值,既避免解散判决的作出,又为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提供制度支持,对我国司法解散裁判标准的完善有极大的推动意义。
参考文献:
[1](2006)浙民二终字第290号民事判决书,载http://www.zjcourt.cn/content/20060509000003/20070416000004.html,于2011年5月11日访问。
[2]丁文联、潘云波:《公司解散的实质性条件—上海二中院判决博星公司等请求解散博华公司案》,载http://rmfyb.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08275,于2011年5月2日访问。
[3]Bryan. A. Garner (Editor- in- Chief):《Black Law Dictionary》,West Group, 1993年版,第404页。《布莱克法律辞典》对于公司僵局的解释:“Deadlock: The blocking of corporation action by one or more faction of shareholders or directors ,who disagree about a significant aspect of corporate policy.”
[4]Merriam-webster:《Merriam-Webster’s Dictionary of Law》,Merriam-Webster Incorporated, 1996年版,第122页。
[5]赵旭东:《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2月8日第3版。
[6]《中国公司法修改草案建议稿》第二百八十条:公司因下列原因而解散:……(六)出现公司僵局,因法院判决而解散。
[7]布莱恩?R?柴芬斯:《公司法:理论、结构和运作》,林华伟、魏昱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39页。
[8] Sandra K. Miller:《How Should U.K. and U.S. Minority Shareholder Remedies for Unfairly prejudicial or Oppressive Conduct be Reformed》,载《Am. Bus. L. J》1999年第36期,第579页。
[9] Douglas K. Moll:《Reasonable Expectations v. Implied in-Fact [10]Contracts: Is the Shareholder Oppression Doctrine Needed》,载《B. C. L. Rev》2001年第42期,第989页。
[11]段威:《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合理期待落空原则——评英国上议院Ebrahimi v Westbourne Gallerises Ltd.案》,载《判解研究》2004年第2辑,第188页。
[12]A.J.博伊尔:《少数派股东救济措施》,段威、李扬、叶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137页。
[13]沈四宝:《最新美国标准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页。
杜景林、卢谌译:《德国股份法?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7页。
[14]王书江、殷建平译:《日本商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页。
[15]L. S. Sealy:《Cases and Materials in Company Law》(the 7th edition),London: Butterworths, 2001年版,第517页。
丁昌业译:《英国破产法(Insolvency Act) 》,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页。
[16]Janet Dine:《Company Law》(the 4th edition),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84页。
[17]沈四宝:《最新美国标准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