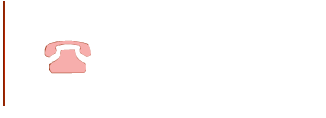隐名投资协议与股份代持协议有效吗?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19-01-05 13:39:39
浏览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0)青民再重字第3号
原告:A
被告:B
原告A与被告B财产返还纠纷一案,原告A于2003年8月1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经公开开庭审理,于2004年5月19日作出(2003)青民四初字第325号民事判决,被告B不服该判决,于上诉期内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经公开开庭审理,作出(2004)鲁民民一终字第268号民事判决,判决维持原一审判决结果。B不服原二审判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09年12月18日作出(2009)民监字第609号民事裁定,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于2010年9月7日作出(2010)鲁民再字第17号民事裁定,撤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鲁民民一字终第268号民事判决和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青民四初字第325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案在重审过程中,由审判员韩向东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周建军担任本案主审,与代理审判员解鲁共同组成合议庭,于2010年12月1日向被告B送达民事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本院于2011年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A的代理人孙运勇、被告B及其委托代理人褚中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烟台C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2002年12月更名为烟台C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是于1997年12月24日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中墨(墨西哥)合资经营企业,中方股东为烟台市药业总公司,外方股东为墨西哥Q集团公司(以下简称Q集团),注册资本人民币407.45万元,中方占49%,外方占51%,法定代表人为墨西哥方的B,总经理为张富国,外方投资始终没有到位。2000年2月15日,A、B以及张富国三人签署协议书,由A出资人民币150万元,B出资4.2万美元,张富国出资人民币20万元,全部以B的名义投资于C公司,该总投入占C公司51%的股份。此前的2000年2月14日,A付给B人民币150万元。1998年10月19日,B收到姜国君向C公司投资的款项人民币10万元,2001年6月23日,A与姜国君签署协议,姜国君将此债权转让给A。A认为,其与B、张富国所签署的协议书虽名为向C公司投资,但A付出的人民币150万元投资并未得到法律所认可,其不是C公司的股东,协议书中称B愿转让部分股份给A是不现实的,转让出资也未得到中方股东的认可,且亦未办理批准手续,A没有获得并行使股东应有的权利。事实上这只是B设下的圈套。依此,B占有、使用其巨额资金,姜国君的投资也只是一般债权。故A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返还人民币160万元,偿付利息损失人民币284087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B在原一审庭审过程中辩称,原告A仍应承担对C公司的投资责任,其享有C公司出资人的权益,原告起诉本案诉讼时效已经届满。
被告B在本案发回重审的庭审过程中辩称,本案事实是:1996年A数次请求B帮忙成立一家中外合资医药企业,承诺外方出资额全部由A承担,B不分红也不承担责任。1997年A签字经办由墨西哥Q集团与烟台市药业总公司成立了合资企业,A任董事、副总经理。注册后A无由拒不出资,墨西哥公司撤销了A的董事任命。C公司注册资本是由烟台市药业总公司出资人民币200万元、墨西哥公司出资4.2万美元、张富国出资人民币20万元、姜国君出资人民币10万元(张富国、姜国君均以墨西哥公司名义出资)。1999年A又多次主动要求隐名出资获益,他欺骗B说没有股份要求,但他必须担任东方公司董事、姜国君退出、墨西哥公司控股三个条件,理由是确保他投入的资金绝对安全可控,他还要求主管全面工作并拥有财务签字权。B和合资中方协调同意后变更了工商登记,再次委派A为董事。A起草了他与B、张富国的《协议书》,付给B150万元人民币,按1:8.745的汇率,换汇171,524.43美元,经A和张富国报请外管局批准,投入到C公司美元资本金账户。A投入东方公司160万元人民币后(含受让姜国君10万元),利用主持公司工作并掌握财务签字权之机,非法将本息超过人民币100万元的资金侵占。后因东方公司经营不善,他欺骗张富国说他主持C公司经营,他认可人民币60万元的亏损,拿走100万元,他退出东方公司。A伪造了董事会决定同意他侵占资金的《议项书》,并仿冒董事长B、董事张媛静签名(这一事实A在烟台市芝罘区法院审理的另一起案件中已作出认可),欲达到侵占公司资金的目的。A起诉本案过程中蓄意隐瞒其隐名投资的真相,虚构B非法占有使用他人资金的事实,欺骗人民法院,干扰了正常的审判活动,致使原审判决作出了与事实相反的判定,致B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在主观上是蓄意诈骗。
被告B在本案发回重审审理期间对原告A提出反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A因其主观恶意诉讼给B造成的名誉损失、精神赔偿、经济损失等共计人民币3400余万元,并要求A承担其他侵权责任。被告B向本院提交反诉状后,向本院提交了免交反诉费用的申请。本院于2011年2月17日向B送达诉讼费催缴通知书,告知其“应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七日内缴纳反诉案件受理费,逾期未交纳的,视为撤回反诉”,被告B至本案庭审辩论终结前未能按《通知书》的要求缴纳反诉案件受理费。本案庭审过程中,合议庭经评议后告知被告B对其所提反诉不予审理,B可另案主张。
原告A在本案原一审庭审过程中提交的证据及被告B的质证情况如下:
证据1:C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一宗,包括: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委派书及登记表、变更登记表、公司章程修改条款及董事会会议纪要等材料,欲证明C公司最初设立时投资情况、资本情况及名称变更的情况。
被告B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欲证明的事项亦无异议。
证据2:A、B、张富国于2000年2月15日所签署的协议书,欲证明该协议书形式上看是投资,A将约定的人民币150万元交付给B,但实际上没有投入公司,该协议是无效协议。
被告B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协议打印的日期是2000年2月12日,实际签署日期为A投入150万元后的2月15日。
证据3:支票存根、银行进账单、B的收款证明,欲证明A已将人民币150万元于2000年2月15日交付给了B。
被告B对于收到人民币150万元的事实无异议,主张该款按约定已经投入到C公司。
证据4:姜国君的证明、A与姜国君签署的协议书,欲证明姜国君将向C公司投入的10万元投资权益转让给A。
被告B对于姜国君出资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姜国君与A所签署的协议书与其无关。
本院认为:B对于A在原一审庭审过程中所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上述证据材料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被告B在原一审庭审过程中提交的证据及原告A的质证情况如下:
证据1:C公司验资报告,欲证明C公司的股东对公司的出资及增资已全部到位。
原告A对验资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
证据2:议项书,欲证明A未经B的同意擅自签署了C公司股东代表B、张媛静的签名,将公司外方股东的出资转到A控股的烟台Q医药有限公司使用。
原告A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所记载的事项与本案无关。
证据3:C公司的证明,欲证明A从2000年正式参与C公司的经营,由他批准调用资金到烟台Q医药有限公司使用,C公司目前亏损严重。
原告A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主张A在C公司任职情况在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中已有记载。B任C公司董事长,故该公司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证据4:付款通知单、单据一宗,欲证明A在C公司任董事期间负责分管公司全面工作并对公司财务有批准权。
原告A对于其曾担任C公司的董事,并在2000年至2003年这一期间负责分管公司财务这一事实无异议。
证据5:证人张富国出庭作证证言。张富国作证称:C公司成立时外方股东出资4万余美元,A顶着B的名义向C公司投入150万元,烟台Q医药有限公司是在C公司成立后设立的,后期两个公司的财务均由A主持,只有A签字,公司才能对外付款,两个公司产生了摩擦,就分开了。A要求财务在他跟前办公,张富国不同意,A提议还他150万元,之后才有了“议项书”。有关“议项书”中所涉及的款项,C公司已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烟台Q医药有限公司。
原告A对于张富国的证人证言质证称,张富国所谈的“议项书”产生的背景与其所述不同。
本院认为:除前述“证据3”外,原告A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上述证据材料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3”需待综合考查其他证据材料后,方可确定其证据效力和证明力。
本案在发回重审审理过程中,原告A、被告B对于在原一审过程中各自提交证据的陈述意见及质证意见均无补充。
原告A在本案发回重审的庭审阶段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被告B在本案发回重审的庭审阶段提交证据及原告A质证情况如下:
证据1:1997年12月由A签字的副总经理委派书,证明A出任C公司副总经理系由公司外方股东墨西哥Q集团委派,并非被告本人委派。
原告A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
证据2:1998年10月,墨西哥Q集团的证明,欲证明C公司注册后,A拒不履行出资义务而撤销其副总经理职务。
原告A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
证据3:中国银行特种转账传票二份,欲证明在2000年2月16、17日,B已将折合人民币150万元的美元投入C公司的资本金账户内。
原告A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鉴于传票的付款人处为空白,不能显示付款主体,且数额与原告主张的不一致。
证据4:2006年烟台市芝罘区法院调查笔录,欲证明《议项书》是虚假的,A冒用他人的签名将C公司100万元资金转走。
原告A对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议项书》是一份意向,而非协议,与本案无关。
本案庭审过程中,被告B申请传召证人张富国出庭作证,张富国就本案相关事实作出如下陈述:
1、关于三方《协议书》,证人称,签署协议书的目的在于明确各方出资比例及享有权益的大小,A要求在C公司中占主导;协议书没有涉及股权转让、转让的价格、时限。
2、关于本案涉及的150万元资金的走向,证人称,在2000年2月16、17日通过烟台市外汇管理局,由A和张富国将人民币150万元兑换成美元通过墨西哥Q集团转入C公司。
3、关于《议项书》,证人称,该份文件由A提意,张富国按A的意思起草,起因是当时A打算把由其投资兴办的烟台Q医药有限公司与C公司的财务分开,A认可由其承担C公司人民币60万元的亏损,把另外100万元的投资转走,然后A退出C公司。A退出公司后,C公司因亏损严重即进入清算程序,不再经营。
4、关于A、B在C公司的任职及业务分管情况,证人称,B任董事长、A任董事,A主导公司的业务经营,B实际不参予公司经营。
原告A对上述证人的陈述质证称,张富国的表述并未在《议项书》中明确记载,亦未能提交证据加以佐证,不能证明所谓“原告认可承担C公司60万元亏损,转走另外100万元”的事实。《议项书》是一份意向,并不对双方产生实际的约束力,与本案无关。
被告B认为证人陈述客观真实,三方《协议书》不是股权转让协议,是一份委托持股协议;协议约定的150万元已投入C公司账户,这一事实张富国在芝罘区法院听证会上已作证,A没有提出异议;A认可由其承担C公司亏损中的60万元份额,其余100万元投资已经转走;C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A,B只是挂名。
本院认为对于B在本案发回重审审理期间所提交的证据材料,A对真实性均无异议,该部分证据材料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本案发回重审审理期间,原告A、被告B均向法庭提出了前往中国银行烟台市分行调取与《特种银行转账传票》有关的其他证据材料的申请。法庭依据原、被告双方的申请向中国银行烟台市分行调取了《特种银行转账传票》、《银行内部结算凭证》、烟台市外汇管理局对墨西哥Q集团《请示》的《批复件》各二份,上述证据材料载明了与本案争议有关的如下内容:2000年2月16、17日,墨西哥Q集团法定代表人B将美元171524.43元作为外方出资,申请由其岳父李书皋的个人账户汇入C公司资本金账户。烟台市外汇管理局批准了该申请。后上述资金经由李书皋的个人账户汇入C公司的资本金账户。
原告A、被告B对于法庭调取的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均无异议,A亦认可上述美元资金经由李书皋的个人账户汇入C公司的资本金账户的事实。
本院认为,鉴于原、被告双方对于法庭依申请调取的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该份证据可作为定案依据。
经审理查明,1997年12月,墨西哥Q集团与烟台市药业总公司约定分别出资21.6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80万元)和人民币200万元共同成立C公司,被告B作为外方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和法定代表人担任合资公司副董事长,原告A作为外方股东派出的董事进驻C公司并担任公司副总经理。1998年10月,外方股东向C公司董事会提交人事变更通知,决定撤销A作为外方董事的职务、撤销A全权代理墨西哥Q集团业务的授权,任命姜国君取代A的职位。上述通知送达C公司后,C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1999年3月,C公司变更了中方的投资主体、双方的出资比例和注册资本总额,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407.45万元,外方股东追加出资折合人民币27.45万元后占公司出资额的51%,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告B。
2000年2月15日,原告A与被告B及案外人张富国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一、B有意与烟台市医药公司合资成立C公司;二、因B系墨西哥华人且资金紧张,故愿在合资公司中转让部分股份给A、张富国;三、A已投入合资企业人民币150万元,B已投入4.2万美元,张富国已投入人民币20万元,全以B的名义投资于该合资企业,占C公司51%的股份;四、为明确三方在投资该合资企业的股份占有比例,以便按各自投入的比例享有权力、承担义务和责任,故将该墨西哥Q集团占有的51%股份合成100%,其中A占股份为 %,B占股份为 %,张富国占股份为 %;五、C公司实际上是三方共同与烟台市医药公司成立的企业,因此公司所作出的重大决定须外方表决时,B应先与A、张富国共同协商达成书面一致后,方可在合资企业中参与表决;?;七、本协议为三方成立C公司对B转让给A、张富国的C公司的股份后调整三方在C公司占股份比例所签订的协议”。2000年2月14日A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将人民币150万元交付给B。2000年2月16、17日,B以其岳父的名义将所收到的人民币150万元折算成171524.43美元汇入C公司资本金账户内。2000年2月10日,A重新进入C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并主持公司财务工作。
2003年张富国与A共同起草《议项书》一份,内容为:“由于C公司与烟台Q医药有限公司一直混在一起经营,经C公司董事会研究,有必要将两公司分离,原则运作方案如下:1、烟台Q医药有限公司、北马路49号Q大药房、二马路Q大药房由A全权负责经营管理。C公司、北马路243号Q大药房、青年路Q大药房、西大街Q大药房、烟台Q医药有限公司业务二部由张富国负责经营。2、?前期公司亏损由烟台Q医药有限公司业务二部承担。部分外方投在C公司的160万元资金除部分作扭亏资金外,余款转到烟台Q医药有限公司使用?。3、以两个法人公司为主体调整资产归属,原则上现有资产哪个公司占用,属于哪个公司。?,5、议项书签定后调整开始,?”。该《议项书》表面载有C公司董事会五位董事(A、B、张媛静、谷庆文、张富国)的签字。在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于2006年6月28日就烟台市医药公司申诉的与烟台Q医药有限公司垫付工资纠纷一案的庭审调查笔录中,A承认前述“B、张媛静”的签字是其在未征得B、张媛静同意的情况下由其签署的。
另查明,1998年案外人姜国君向被告B交付其拟向C公司投资款人民币10万元,该款项被告B收到后投入C公司。2001年6月23日,原告A与案外人姜国君签署协议一份,内容为:姜国君将其持有的以B名义于1998年10月19日投资于C公司的人民币10万元转让给A,姜国君在C公司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A。
本案庭审结束后,原告A及被告B的诉讼代理人均向法庭提交了代理词。原告诉讼代理人认为:一、三方《协议书》的内容是虚假的,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无效的。1、三方《协议书》的核心内容是B转让在C公司的股份。而根据工商登记材料,C公司成立于协议书之前,公司的中外股东的出资已到位,外方股东亦没有授权B转让股份的股东会决议,故所谓股份转让是虚构的。2、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规定,原告作为个人不能成为合资公司中方的股东,被告B也不是C公司的股东,故《协议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原告A因无效协议而支付的160万元应当返还。二、被告B明知不具备签订《协议书》的合法资格以及《协议书》内容违反法律规定,而与原告签订《协议书》,应当承担过错责任。三、原告损失巨大,B应承担其全部损失。四、B承担返还A160万元的义务有法律依据,不论该160万元是否投入C公司,B均应予以返还。五、B所提交的《银行特种转账传票》不是新证据,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六、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被告诉讼代理人认为:一、《协议书》合法有效,非股份转让协议。三方签订《协议书》的本意是通过墨西哥Q集团投资C公司获利,就《协议书》的内容来看,此协议实为投资协议或委托持股协议,而非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在山东省高院审理时,原告A的原代理律师自始至终都没有否认《协议书》的效力。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规定,自然人不能成为中外合资企业的中方股东,这也是A要签订协议书的根本原因。其只能将资金投资入墨西哥Q集团,和张富国、墨西哥Q集团作为一个出资整体以墨西哥Q集团这个外资身份对C公司出资,并据此行使股东权利。A单方要求退还160万元投资款违反了《协议书》的约定和《合同法》的规定,依法不应支持。二、A起诉对象错误,B非本案当事人。B为墨西哥Q集团的法定代表人,C公司的股东是墨西哥Q集团和烟台市医药公司,B不是C公司的股东。因此,B不可能以自己的名义和A签订《协议书》。《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是就C公司的资金构成及权利行使作出的详细约定,《协议书》立约的目的是就共同以墨西哥Q集团与烟台市医药公司成立烟台C公司达成的协议,几乎每个条款中都涉及了墨西哥Q集团。B是墨西哥Q集团的总裁,《协议书》中的乙方虽名为B,但B签署《协议书》的行为属代表墨西哥Q集团的职务行为,法律后果当由墨西哥Q集团承担。A签约时对B不是C公司的股东是知情的,C公司是在A的倡议下成立的,墨西哥Q集团派出的董事为B和A,这些均能够证明A在1997年C公司成立时就已知道该公司的外方股东是墨西哥Q集团。三、150万元投资款去向明确,B没有侵占。A交付的150万元按当日国家外汇牌价1:8.745的比例从他人处兑换成了171524.41美金进入了C公司的账户,最终由A自己实际控制。证人张富国也当庭证明:“资金进入C公司后,一直由A自己控制。后C公司和烟台Q医药公司分家时,A对投入到C公司的160万(含转让的10万)自认60万元的亏损,100万元转到其控制的烟台Q医药公司”。A非法伪造B和其他人的签名,“炮制”出《议项书》,违法将100万元据为己有。四、A的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按原告的观点,在2000年2月12日签订协议书之后随之得知B不是股东,所以其160万元应当退还。也就是说这时A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到其2003年起诉本案时,已明显超过2年诉讼时效。
本院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A提交的工商登记材料、三方协议书、银行进账单、支票存根、A与姜国君所签协议及被告B提交的工商登记材料、议项书、证明、付款通知单及单据一宗、人民法院调查笔录、委派书、张富国的证人证言、特种银行转账传票、以及本院调取自银行的单据、开庭笔录等证据材料加以证实,上述证据材料已经本院审查和开庭质证,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为财产返还纠纷,因被告B系墨西哥公民,本案依照涉外商事纠纷案件审理。因本案中争议款项的交付地在山东省烟台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讼诉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相关规定,原告起诉本案时,涉案款项发生地在本院司法辖区内,本院依合同履行地为连接点,取得对本案的管辖权。庭审过程中,各方一致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体法律解决本案实体争议,本院对各方当事人的选择予以确认。
本案原、被告双方的诉争围绕2000年2月三方签订的《协议书》以及原告A交付给被告B的150万元资金的走向展开,故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二,其一,三方《协议书》应当如何定性;其二,涉案的160万元是否已作为A对C公司的投资投入合资公司,A本人对该事实是否应当知情。
关于焦点问题一,《协议书》的第二条在字面上虽表述为“转让部分股份”,鉴于A在C公司成立时即以外方股东派出董事的身份任职公司的副总经理,A对于C公司外方股东并非B个人这一事实应当是明知的,故A应当知道B个人实际上没有“股份”可以转让。同时,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不允许我国公民以个人身份作为中外合资公司的股东,即使B欲通过其实际控制的墨西哥Q集团将股份转让给A,基于上述法律的规定,A亦不可能通过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方式成为C公司的“显名”股东,签约的三方当事人对于法律的这一规定均应当是明知的。但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前述规定并不必然导致《协议书》无效的法律后果,原因在于法律的这一规定规制的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方股东的“市场准入门槛”问题,A与B或墨西哥Q集团约定受让外资股份,该约定因违反了法律关于行政管理的相关规定,而无法办理股权过户手续,但该约定本身并未侵害到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协议书》的第二条约定的内容存在履行上的障碍,其根本原因不在于C公司的中方股东对于三方《协议书》是否知情,亦不完全在于B个人是否有“股份”可供转让,而是由于法律的规定使得A无法成为C公司的“显名”股东,A欲实现参股C公司的目的,只能选择“隐名投资”的方式。故三方《协议书》不应仅依据前述第二条的表面记载而定性为股权转让协议。从《协议书》第四、五条的表述看,这是三方确定以C公司外方股东墨西哥Q集团的名义持股,A、张富国以隐名股东的身份按投资比例分享墨西哥Q集团在C公司中的股东权益。关于“隐名投资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在2000年之前,不论是我国《公司法》还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均没有对这一现象作出否定性的规定。因此,本案“隐名投资协议”,即三方《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应当依据我国《合同法》中关于合同效力的原则性规定确认其是否具备法律效力。《协议书》的第四、五条明确约定A、张富国以“隐名投资”的方式,分享股东权利。在实际操作中,A于《协议书》签订之时将150万元投资交付给了B,意图通过B作为外方股东代表的身份将该笔资金投入C公司,在交付上述“隐名投资”款后,A以入主公司的方式实现了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目的。《协议书》的这一约定是A、张富国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无效情形,应当认定《协议书》中A、张富国“隐名投资”、分享股东权益的约定在三方签约人之间具备法律约束力。
关于焦点问题二,诉争的160万元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姜国君于1998年交付给B的10万元“隐名出资”,该部分出资从2001年6月A与姜国君所签订的协议书的表述看已经于1998年10月份投资于合资公司。第二部分是2000年2月14日A交付给B的150万元“隐名投资”。对于该笔资金的走向,原告A在起诉状中称150万元资金由被告B“占有、使用”。被告B在原一审庭审过程中主张依据三方《协议书》第三条“甲方(A)已投入合资企业150万元”的表面记载,证明该笔资金其已投入合资企业。根据B在原一审庭审质证过程中的表述,其签署该份《协议书》的时间是在2000年2月12日,A交付投资是在2000年2月14日。显然,协议签署时资金不可能进入公司资本金账户。众所周知,我国在2000年前后对于“资本”项下外汇资金的进出境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措施,一般情况下,中外合资企业外方投资者的出资应当是从境外汇入外币资本金,且须经过外汇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后,银行方可将外币投资汇入合资公司的资本金账户内。所以,即使按照《协议书》表面载明的署名日期:2000年2月15日看,2000年2月14日A才将150万元资金交付给B,按照一般的惯例,B不可能在一天的时间内从境外调集外汇资金并完成外汇管理的各项审查批准手续,并将外汇资金汇入合资企业资本金账户内。故仅凭《协议书》第三条的表面记载不能确定在协议签署时,约定的外汇资金已实际汇入合资公司资本金账户内。关于《议项书》中涉及的160万元问题,《议项书》的记载为“部分外方投在C公司的160万元”,这里并没有直接涉及到A交付给B的150万元,且B在原一审庭审过程中提交的C公司验资报告载明外方股东出资已到位。故单凭此项记载亦不足以证实本案所涉150万元资金的走向问题。实际上,从本院依申请调取的银行证据看,B在收到A交付的上述150万元资金后,另行筹集了17万余美元,并以向烟台市外汇管理局特别审批的形式,将该笔资金通过B岳父的个人账户内在境内完成了转账手续,资金实际汇入合资公司资本金账户的时间也是发生在2000年的2月16、17日。综上,只有本院调取自银行的证据材料才能够完整地证明B已完成了三方《协议书》项下的受托投资义务。
关于原告A对于150万元“隐名投资”的走向是否知情的问题,本院认为,综合本院调取自银行的证据材料、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的调查笔录及张富国的证人证言,能够确认《议项书》中关于“外方投在C公司的160万元资金”即是A受让于姜国君的10万元和其本人投入的150万元“隐名出资”,理由基于以下已经查明的事实:第一、三方《协议书》中对于C公司的外方股东实际投入公司的出资额确定为4.2万美元,这一数字与160万元出资的表述有极大差距;第二、投入到C公司的150万元出资表面上是以外方股东的名义进入公司资本金账户;第三,该部分资金是B收到A的委托投资款后,以“曲线”方式投入C公司;后期,A又受让了姜国君的10万元“隐名出资款”,合计为160万元出资。A在本案所涉《协议书》签署之前便以C公司董事的身份重新进入C公司,并在《协议书》签署之后掌管公司财务长达三年左右的时间,期间,其对于B以其岳父账户汇入公司资本金账户内的150万元资金的来历是不可能不知情的。同时,在《议项书》中A和张富国亦对于该160万元作出了“部分作扭亏资金外,余款转出”的处理,这表明:第一、A认可其投资于C公司的资金总额为160万元,第二、A至少在签署《议项书》时对于其投资于C公司的160万元资金已入账的事实是充分知情的。
关于原告在其诉讼主张和代理意见中所提出的“被告明知不具备签订协议的资格,明知协议书的内容违法,而签订协议书,应承担全部过错责任”的主张,本院认为,B全资控股的墨西哥公司持有C公司的股份,A对于这一事实应当是明知的。因此,《协议书》实际上是A、张富国与B所签订的“隐名投资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颁布的《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确指出:合同约定一方实际投资,另一方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不具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合同有效。一方当事人仅以未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为由主张该合同无效或未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这一司法解释的原则性规定看,法律对于当事人之间签订“隐名投资”合同,并据此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是不禁止的。关于A是否享有并行使了C公司出资者权益的问题,B在本案原一审过程中提交的大量发生于2000年至2002年间的公司财务凭证看,A在与B签署了《协议书》之后,以C公司董事的身份执掌公司的财务,这一事实证明A在这一段时间内实际享有并行使了出资者关于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原告A所提因“《协议书》无效,其出资行为未得到法律认可”,进而要求B返还投资款的主张,本院认为,B依据三方《协议书》所承担的是一种受托投资义务,在其将资金汇入公司后,其合同项下的义务已履行完毕,不存在返还投资款的问题。至于原告是否如其在诉讼代理词中所称“损失巨大”,实际上,A在以董事的身份重新进入C公司后已经享有并行使了出资者的权益,其在退出C公司时通过未经许可使用公司其他董事签名并制作《议项书》的形式,认可由其承担C公司的部分亏损并意图将其投入到C公司的剩余出资抽出,这一表示说明即使其投资有所损失,A对该部分损失也是自认的。关于原告所提B提供的《中国银行特种转账传票》不是新证据的主张,本院认为,本案是经审判监督程序审查后发回重审的案件,案件审理按照一审程序进行,故A主张所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不适用于本案的情形,该主张不应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A对被告B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430元,由原告A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A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B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副本,缴纳相应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0一一年四月十二日